最炎热的日子里,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,人在街上走,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,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,墙也是热的,人在街上走,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,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,若有若无的,飘荡在耳边。饶舌的、嗓音洪亮的、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,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,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,一味地追求通风,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,张着大嘴巴打着时断时续的呼噜,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,田径裤的裤腿那么肥大,暴露了男人的机密也不知道,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,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,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,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,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。
下午三点钟,阳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,阳光从全线出击变为区域防守,街上的房屋乘机利用自己的高度制造了一条“三八线”,“三八线”渐渐地游移,线的一侧是热和光明,另一测是凉快和幽暗,行人都非常势利地走在幽暗的阴凉处。这使人想起正在电影院里上映的朝鲜电影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,那些人为银姬在“三八线”那测的悲惨命运哭得涕泅横流,可在夏天他们却选择没有阳光的路线,情愿躲在银姬的黑暗中。最炎热的日子里,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,人在街上走,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,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,墙也是热的,人在街上走,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,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,若有若无的,飘荡在耳边。饶舌的、嗓音洪亮的、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,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,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,一味地追求通风,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,张着大嘴巴打着时断时续的呼噜,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,田径裤的裤腿那么肥大,暴露了男人的机密也不知道,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,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,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,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,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。
下午三点钟,阳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,阳光从全线出击变为区域防守,街上的房屋乘机利用自己的高度制造了一条“三八线”,“三八线”渐渐地游移,线的一侧是热和光明,另一测是凉快和幽暗,行人都非常势利地走在幽暗的阴凉处。这使人想起正在电影院里上映的朝鲜电影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,那些人为银姬在“三八线”那测的悲惨命运哭得涕泅横流,可在夏天他们却选择没有阳光的路线,情愿躲在银姬的黑暗中。最炎热的日子里,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,人在街上走,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,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,墙也是热的,人在街上走,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,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,若有若无的,飘荡在耳边。饶舌的、嗓音洪亮的、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,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,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,一味地追求通风,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,张着大嘴巴打着时断时续的呼噜,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,田径裤的裤腿那么肥大,暴露了男人的机密也不知道,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,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,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,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,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。
下午三点钟,阳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,阳光从全线出击变为区域防守,街上的房屋乘机利用自己的高度制造了一条“三八线”,“三八线”渐渐地游移,线的一侧是热和光明,另一测是凉快和幽暗,行人都非常势利地走在幽暗的阴凉处。这使人想起正在电影院里上映的朝鲜电影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,那些人为银姬在“三八线”那测的悲惨命运哭得涕泅横流,可在夏天他们却选择没有阳光的路线,情愿躲在银姬的黑暗中。最炎热的日子里,整个街道的麻石路面蒸腾着热气,人在街上走,感觉到塑料凉鞋下面的路快要燃烧了,手碰到路边的房屋墙壁,墙也是热的,人在街上走,怀疑世上的人们都被热晕了,灼热的空气中有一种类似喘息的声音,若有若无的,飘荡在耳边。饶舌的、嗓音洪亮的、无事生非的居民们都闭上了嘴巴,他们躺在竹躺椅上与炎热斗争,因为炎热而忘了文明礼貌,一味地追求通风,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向大街的门边,张着大嘴巴打着时断时续的呼噜,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不知道,田径裤的裤腿那么肥大,暴露了男人的机密也不知道,有线广播一如既往地开着,说评弹的艺人字正腔圆,又说到了武松醉打蒋门神的精彩部分,可他们仍然呼呼地睡,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。
下午三点钟,阳光发生了可喜的变化,阳光从全线出击变为区域防守,街上的房屋乘机利用自己的高度制造了一条“三八线”,“三八线”渐渐地游移,线的一侧是热和光明,另一测是凉快和幽暗,行人都非常势利地走在幽暗的阴凉处。这使人想起正在电影院里上映的朝鲜电影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,那些人为银姬在“三八线”那测的悲惨命运哭得涕泅横流,可在夏天他们却选择没有阳光的路线,情愿躲在银姬的黑暗中。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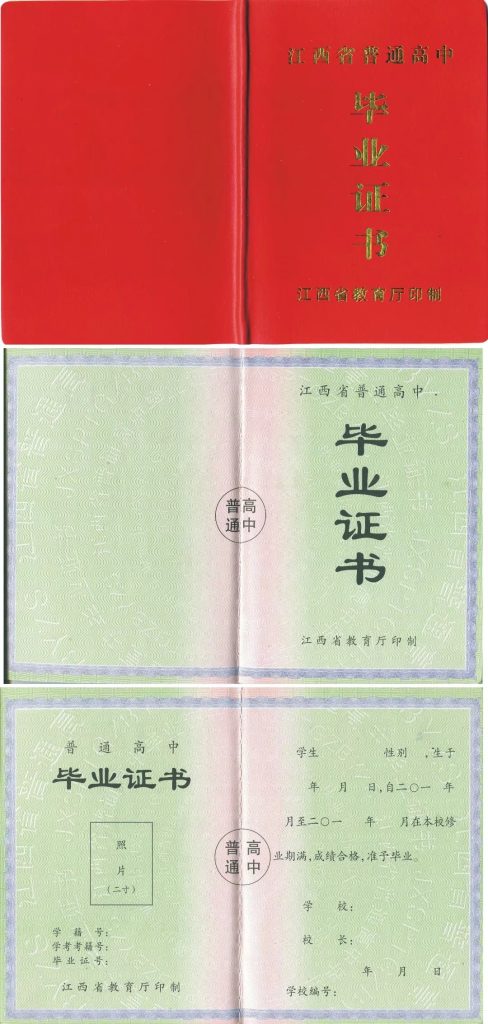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没有回复内容